散文精选 ▎高 沙 奶 奶 (文/姜贻伟)

高 沙 奶 奶
文/姜贻伟
高沙镇在邵阳市的洞口县,洞口县最古老的重镇大概也就是高沙镇了。
我不在那里出生却在那里长大。五岁之前的童年生活,是在高沙镇黄家码头的一家药铺里度过的,我那慈祥美丽的奶奶(其实是我的继外祖母)带着我们过着优裕又恐惧的生活。
在我的记忆里,高沙所有的房子都是由粗厚的木板搭成的,且失去了原色,一律的墨黑无比,像老农被日光久烘了的背脊。每天傍晚,当街市的喧嚣消退之时,湄水上空的暮蔼涌上了黄家码头,涌进了药铺。在外公家做长工的七舅爷,此刻就会听到奶奶亲和的呼唤:“老七,快把伟宝宝找回来,天快黑了哩。”七舅爷朗声应了,就高喊着我的小名,到我常去玩耍的地方把我抱了回来,。然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门板关铺子。那一二十块又厚又重的宽门板,就被七舅爷排队似的依次嵌进门槽,发出哐哐的响声,沉重而又干脆。每装上一块,铺内的光线就暗一份。铺内那些大大小小的绘满图案的药罐子,和写满药名的一大排中药柜,也渐渐地模糊起来。当最后一块门板巨人般地嵌上去,药铺就完全被黑暗吞没了。这时,我的心底就会腾起一股无比强烈的恐惧感。我就会不由自主地跑上去,紧紧地抱住七舅爷的大腿,将一双惊惶的大眼睛贴近门缝,近乎绝望地攫着门外那一线也快消亡的残光。
小时候,我真的特别害怕夜晚,害怕黑暗。
但我三岁之前不怕。三岁之前我还不知道什么叫黑暗,什么叫害怕。奶奶告诉我,那时每天吃过晚饭,天空的晚霞还没有褪尽,她和七舅爷就抱着我去镇上的剧院看大戏。在到剧院的两三里路上,奶奶的步伐雍容而缓慢,她朝每一个熟悉的街坊笑着打招呼。于是,就有许多人凑过来抱我亲我逗我,对奶奶说许许多多恭敬和夸赞的话。“伟宝宝,你不晓得,”奶奶在我长大以后对我说,“小时候你长得好乖态啊,好逗人喜欢哦!奶奶走一路高兴一路。”到了剧院,我又被当演员的八舅爷抱到后台,被一群嘻嘻哈哈的花脸花旦小丑们当宝耍,直到我眼皮打架没精神理睬他们。因此,我三岁以前的夜生活特别丰富,晚上不让出去,就又哭又闹。这就苦了七舅爷,晚上只要不唱大戏,他就得盯着我和街上的细把戏捉迷藏玩游戏,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如果我有个闪失,崽呀崽,奶奶就会一边哭着哄我,一边就把七舅爷骂个狗血淋头。有一次,事情闹大了。七舅爷见我和细把戏玩得正欢,估计不会出问题,就开小差和他的对象约会去了,不料我却摔掉了两颗门牙。奶奶从此就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让七舅爷再碰我了,看见他就横他的白眼,气呼呼地总没一个完。这一次我也惨了,惨的不是两颗门牙,而是奶奶从此不让出去玩了,除了看大戏。最要命的,是奶奶专门讲鬼怪的故事来诱惑我,以转移我夜晚外出的念头。开始,奶奶讲的故事美丽而神秘,什么狐狸精变成美女和白面书生谈爱成家,但白面书生始乱终弃,最后坏人没好报,死了变成了一只白尾狼。但这类缠绵的爱情故事对当时的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,听多了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,我就又吵着要到外面玩去了。我唯一的且最有威力的武器就是哭了。我的哭声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能惊天动地,除了打(但奶奶从不打我),足可击败奶奶任何的围堵阻截和哄骗诱拐。奶奶终于绝望了,情急之下,奶奶不知把一个什么东西往门外一丢(我没看见),啊的一叫,失声呼道:“鬼!鬼来了——”又慌忙把我的头紧抱在她温暖的怀里。我不知发生了什么,但门外黑古隆咚里突然发出的奇怪响声,以及奶奶惊惶的呼叫和搂抱,这个鬼就一下子就钻进了我的大脑,直叫我在一阵强烈的冷颤之后,全身虚汗淋漓。奶奶怕真的吓坏我,就大声骂起鬼来,又百般温柔地哄我入睡。这都是我长大之后奶奶告诉我的。她还告诉我有一次差点被鬼吓死的故事。说实话,我对这件事已经有了记忆。而且其中一两个场景更是刻在我大脑的深处。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,我快满四岁。奶奶说,外公这个叫做福源堂的药铺,因为公私合营的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,全家人都出动了,把我孤零零地丢在后堂。这时有个小伙计敲响了窗户,说街上飞来了好多好多萤火虫,大家都追着捕呢。我爬到窗台上一看,果然见一群小把戏在月光下奔跑,一大团萤火虫被赶得四下逃窜。正好奶奶那天忘了给后门上锁,我也忘了夜之鬼怪,爬上凳子开了门栓就走,投入了捕捉萤火虫的行列。
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这么亮的萤火虫。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它们在夜空中画着明明暗暗的弧线,像魔术师手中绽出的缤纷火花,像夜空中燃放的串串爆竹。我年龄小,抓不到,就充当了发现者的角色,兴奋地大声告诉伙计们,看,这里的一只好大;看,那里的一只好亮。说来也是有鬼,追来追去,我们就追到了码头上。这时,我发现了一只特大的家伙,正在码头旁边的一间低矮店铺的屋檐下藏着,像一个走不动的胖子,蹲在墙脚下休息。我心中一喜,就蹑手蹑脚地走过去,想一个人捕获这美丽的猎物。但是,当我笨笨地用双手去捧捉时,这家伙一下子就弹到了码头上,且急急地向码头下方的湄水河飞去。也就是这个时候,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这个萤火虫王了,这时大家一起高喊着向码头涌来。我一急,就走下了码头的石板台阶,生怕大家抢了先。我还记得,在我下码头时,我听见了湄水河隐隐的涛声,甚至看见了河水变幻的光影。因为此刻我已经感到一丝恐惧和不祥,感到如果再走去,那只萤火虫也许会把我带进河底。我这一想,全身就起了鸡皮疙瘩,两条腿一下就抖起来。哪知就在这一刹那,不知哪个砍脑壳的一声大喊:“鬼来了!”随之而来的是众人的一片惊叫声,以及逃离码头的脚步声。这时,我只记得我身后黑压压的一片人瞬间就蒸发了,然后眼前一黑,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我苏醒后睁开眼睛的第一幕,就是泪眼婆娑的的奶奶一把抱我入怀。她嘤嘤地哭着,絮絮地说着,骂那些恶作剧的砍脑壳鬼,骂自己老糊涂,忘记后门上了锁。她告诉我,刚才已经请师公给我打了三个卦,一阴一阳一保卦,阎王老子下令把催命鬼喊回去了。“没事了,没事了,我伟宝宝福大命大。”奶奶说着说着就笑了,眼水倏的就绽开了花。过了几天,奶奶又请了个瞎子先生给我算命。那情景我如今仍历历在目。算命是在后堂的大门口进行的。外公家的后堂有个又高又宽的台阶,一条长板凳横过青石门槛,算命的先生拿把破二胡坐在上面,龙格龙格龙地拉了老半天,然后一边用一双枯黑的手在我身上摸着,一边对我奶奶阴阳怪气地叽咕着什么,声音低低的,怪怪的,老半天硬是没让我听懂一个字。最后的结果是奶奶找来了几段黑线,按照算命先生的嘱咐,依次把我的颈脖、手脖、脚脖扎起来,扎成五个圈,像女人身上的饰物,丑死个人。奶奶说,这叫守魂,以后鬼来了就不怕了。
我这次碰了鬼,奶奶对此深信不疑,我又怎么能疑而不信?但我总疑心那瞎眼的八字先生说了我许多不祥甚而 致命的话,不然,何以让我守魂?又何以一天到晚不离我半步?我像奶奶手上的那颗金戒指,跟着她吃饭睡觉上厕所。这习惯直到我上了初中。那时,我已经离开高沙,到我父亲工作的一个煤矿读书。奶奶也因为外公去世嫁给了一个乡村教师。我上初一那年冬天,老人家从乡下来看我。晚上睡觉前,我要到外面的厕所小解,正在用烘笼暖被子的奶奶一听,非要亲自带我去,而且最恼火的是霸蛮要我像八年前那样跟她进了女厕所。睡觉时她又要我抱着她的脚。奶奶的脚比过去粗糙多了,但不知为什么,我把奶奶的脚抱得紧紧的,那一晚睡得很香很香。这是奶奶最后一段时间带我睡觉上厕所,因为上初二之后,我对自己的孱弱和胆怯不仅深感羞愧和痛恨,而且迁怒于奶奶的溺爱。所以,当奶奶再次以过去的方式和要求表示她对我的呵护时,我的反抗刹那间升腾到极致,那种毫无退让的表情和动作,让奶奶始而疑惑,再而惊惶,继而颤抖,她不知哪里得罪了自己孙子了。她哭了,哭得十分伤心,不停地用手绢擦拭泪水。“伟宝宝长大了,不要奶奶带了……”她喃喃着,喃喃着,最后终于在万分无奈中妥协了,笑了。
说实话,我的觉醒和反抗不是毫无来由的。我的胆子太小了,小到我经常在独处时看到鬼影。那鬼影有时像袅袅的一股烟雾,有时像竖立的一条蟒蛇,有时却像追着人奔跑的猛兽。我每次在刹那间看见它们时,都吓得我全身发抖,脸色发白,病个十天半月。最要命的,每当父母不在家,由我负责弟弟们的生活时,我不知道自己是在怎样的惊慌和恐怖中度过的。一到夜晚,我拿着一根竹竿,带着弟弟到每个房间的床下柜底进行清剿行动,生怕有人或鬼藏在其中,好在我们睡觉时下毒手。这个行动结束后,我们又展开堵门行动。那就是用长板凳一条顶一条,从大门开始,一直顶到对面的墙脚。然后才战战兢兢地钻进被子,蒙头睡下,竟然连电灯也不敢熄灭。我母亲知道这事后,就叹息着对父亲说:“这都是他奶奶娇的。”父亲却狠狠地说:“哪是娇的,是害的!”母亲听不得这种口气,说:“自己的崽自己又不带,还说人家害的,你良心都狗吃了。好歹我后娘全是一片好心。”
我同意母亲的话,这是一方面,但另一方面,我又非常恨奶奶,恨高沙,恨鬼怪,恨黑暗里那些捣蛋的砍脑壳鬼。我要成为三国水浒中那样的英雄好汉,就必须告别这一切,告别懦弱和胆怯。然而,非常可惜的是,直到如今,我的胆子虽然大了许多,却怎么也没成为英雄,成为好汉。说句实在话,黑暗是永远存在的,恐惧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普遍的心态,而鬼怪的有无,于科学则无,于社会则有。
那年,我在隆回乡下的奶奶重病。老人家九十高寿了,自知不久于人世,就很想见见她都带过的我们几个孙孙。带着深深的愧疚(几十年了,我极少孝敬过她老人家 ),我去了。当我跪在全身肿胀的奶奶脚下,看着她苍老的面容,我不禁泪流满面。奶奶的眼睛肿得仅剩下一只还留着一条细缝。她用手想抚摸我,却没有力气。我便拉着她的手,在我的头上、脸上、身上摸着。她老人家一边摸一边说:“这是我伟宝宝,我伟宝宝小时候长得好乖态……”我再也看不见奶奶过去那双慈祥美丽的眼睛了,就哽咽着问:“奶奶,你还看得见我吗?”奶奶的声音突然亮起来:“看得见,看得见!”这时旁边的亲戚告诉我们,昨天奶奶的眼睛还肿得没一丝缝,晚上听说你们要来,怪了,早晨就睁开了这一条缝。怕这是天意啊。我们听了大为惊讶。奶奶呢,此时嘴角却浮出一丝我熟悉的难得的微笑。
我们来时,天空晴朗;我们走时,大雨倾盆。我独自打着雨伞快步走在前面,心里充满了悲怆和凄凉。我想,这肯定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老人家了。于是,我就着滂沱的秋雨,毫无掩饰地号啕大哭起来。
奶奶是在我回来后的一个星期去世的。第二年清明,我给她老人家去扫墓时,她静静地躺在一大片青悠悠的草地上。之后,我又特地去了一趟久违的高沙。在残存的摇摇欲坠的木板屋前,在依稀可辨的黄家码头上,在静静流淌的湄水河畔,在面目全非的福源堂药铺里,我似乎想找回儿时的记忆,又似乎心如止水,什么也不想去寻找了。看来,只有等到夜晚,等黑暗降临的时候……

作者简介
姜贻伟,武冈籍,年七十,居郴州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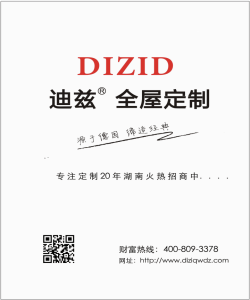
 合作伙伴
合作伙伴








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
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